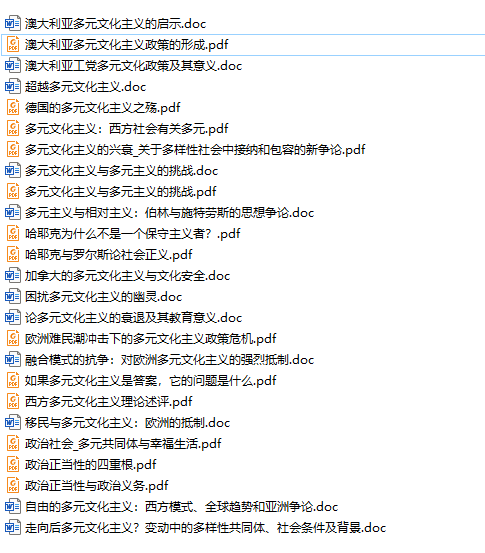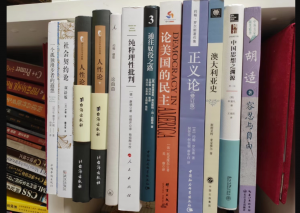这段时间阅读伯林的《自由论》及相关书籍,发现伯林的思想广博又深邃,他是哈耶克和波普尔的好友,他的很多想法甚至超越了穆勒,我特别欣赏他坚持在自由的前提下,坚守多元和容忍。伯林有两篇重要的文章,重要得我不得不转到这里来,为此我专门进行了OCR识别,并且人工校对。
第一篇文章是他总结自己的思想史,回顾最重要的两个观点:一是否定历史必然性,即否定决定论,二是再次阐述自己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观点。这篇文章摘自伯林的作品《我的思想之路》(1987),全文收录于《观念的力量》(伦敦,2000:温多斯;普林斯顿,2000: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决定论
政治自由是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个讲演的主题。第一个讲演题目是《历史必然性》。在这里,我陈述的观点是:决定论是一种千百年来为无数哲学家广为接受的学说。决定论宣称每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从这个原因中,事件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规律及这些规律的运用——构成整个自然科学——建立在自然科学所探讨的永恒秩序的观念之上。但是,如果自然的其余部分都是服从于这些规律的,那么唯有人类不服从它们吗?当一个人就像绝大多数平常人(虽然并非绝大多数科学家与哲学家)那样假定,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他并不是非要这么做不可;他从椅子上起来,是因为他选择这样做,但他并不是必须要做这样的选择——当他这样假定时,他就被告知:这是一种幻觉;随着心理学家的必要工作的完成(它尚未完成,但至少从原则上讲是可以完成的),总有一天他会发现,他的所是和所做都是必然如此的,是不可能不如此的。我相信这个学说是错误的,但我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证明这点,或者说我并没有驳斥决定论,而且我也怀疑这种证明或者驳斥是否可能。我的唯一用心是问自己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或其他人认为人类是完全被决定的?如果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么,这与一般所理解的正常的道德情操及行为是否相容?
我的观点是,主要有两个理由支持人的决定论的学说(注:伯林自己并不认同这两种学说,而是在叙述这两种学说的过程中对它们进行反驳)。
第一个理由是,既然自然科学是整个人类历史中也许最成功的故事,那么假设只有人不服从由自然科学家发现的自然规律,便是非常荒谬的。这的确就是十八世纪的phibsophes(哲人们)所坚持的。当然,问题并不是人是否完全不受这种自然规律决定——只有疯子才会坚持人不依赖他的生物学或心理学结构,不依赖于环境或自然规律。关键的问题是:他的自由是否因此完全被杜绝?是不是还存在着某个角落,在其中他可以做他选择的事情,而不是被前在的原因决定去做这种选择?在自然领域中这也许是个很小的角落,但是除非这个角落存在,他的作为自由的存在物的意识——这种意识无疑是普遍的;绝大多数人相信这种观点,即虽然他们的行为中有些是机械的,有些却是服从他的自由意志的——才不至成为一种巨大的幻觉^这种意识自从人类开始时,即从亚当偷食禁果时就存在了。亚当虽然被告知不要偷食禁果,似偷食了以后也没有这样回答:“我禁不住这样做,我并不是自由地这样做的,是夏娃强迫我这样做的。”
第二个理由是,它把人们做的好多事情的责任,推到非人的原因上面,从而使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无需负责任的感觉。当我犯了一个错误,或者做了一件坏事,或犯了什么罪,或做了我或其他人认为是坏的或不幸的事情,我会说:“我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呢?我就是被教育这样做的”;或者,“这是我的天性,自然规律应该对此负责”;或者,“在我所属的那个社会、阶级、教会、民族中,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且没有人谴责这样做”;或者,“从心理学上,我是受我的父母彼此之间的行事方式以及他们对我的行事方式决定的,是受我置身其中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决定的,或者是被迫这样做的,无法做其他选择的”;或者干脆,“我是在执行命令”。
与此相反,大多数人相信每个人都至少能够做出两种选择,两种他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当艾希曼说“我杀死犹太人是因为我被命令如此;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自己也会被杀死”时,人们可能会说:“我觉得你不太可能会选择被杀,但是从原则上讲如果你决定这么做,你就可以这样选择。并不真的存在像自然界中那样的强迫,导致你做出你的行为。”你可能会说,当面临巨大危险时,期望每个人都如此行事是不合理的。的确如此,但是不管多么不可能,在他们“能够”作此选择这一字面意义上,他们都应该决定这么做。殉难是不能期望的,但是殉难是可以接受的,不管其概率有多么小。而且这正是它如此值得称道的原因。
这就是历史上人们接受决定论的理由。但是如果他们接受决定论,那么至少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困难。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对任何人这样说:“你已经这样做了吗?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不可?”隐藏在这种说法下面的假定是,他其实可以不这样做,或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我觉得正是我们的全部日常道德观点(在其中我们可以谈及责任与义务、对与错、道德褒贬)——也就是当人们不是被迫行事时(他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他们因其所作所为而受到的称赞或谴责、奖励或惩罚——我们日常道德依赖于其上的这种信念与实践的网络,假定了责任的观念;而正是责任使得在黑与白、对与错、快感与义务之间做出选择成为必要;同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得在生活方式、政府形式与整个道德价值星丛中做出选择成为必要——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根据这些价值星丛来生活的。
如果决定论被接受,那么,我们的词汇就要做出非常根本的改变。我并不是说这事从原则上讲不可能,但是它的确不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承受。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学将代替道德。你会羡慕或赞扬某些人的帅气、慷慨或精通音乐,但这不是他们的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被造就”的结果。道德赞扬也将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形式:如果我因为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而赞扬你,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值得惊叹的是你被如此造就,以致无法避免这样做;而且我非常高兴我遇到的是某个确确实实被决定要去救我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决定故意朝另一边看的人。值得尊敬与不值得尊敬的行为、享乐主义与英雄般的殉道、欺诈与真诚正派等等,所有这些都变得像漂亮与丑陋、高与矮、老与少、黑与白、英国或意大利父母所生一样,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因为一切都被决定好了。我们可能会希望事情变得如我们所愿,但我们不能为此做些什么——我们被如此造就,以致除了依某种特殊方式行事外无法做任何别的事情。事实上,行动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选择;但是如果选择本身是被决定了的,那么在行动与纯粹的动作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对我来说非常矛盾的是,某些政治运动一方面要求牺牲,另一方面却又持决定论的信念。例如,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决定论——社会在达到完美境界之前必须经过若干不可避免的阶段——基础上的,它责令人从事痛苦而危险的行动、强迫与斗争,这样一些对于行动者与受动者同样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真的不可避免地带来完美社会,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还要为这样一种据说不需要人帮助也会达到其适当而幸福的终点的过程牺牲性命呢?不过,存在着一种古怪的人类情感,即,如果天意在你这一边,你的事业必胜,那么,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你必须牺牲你的生命以缩短这个进程,从而带来新秩序临近的阵痛。不过,是不是那么多的人真的都能被说服去面对这些危险,以缩短那种无论他们行动或不行动都会导致幸福的进程呢?这个问题总是使我、同时也使其他人感到困惑。
我在这个讲座中讨论的问题,一直是具有争论性的问题,它以往被激烈地讨论与争论着,也仍将被激烈地讨论与争论。
关于自由
我的另一篇讨论自由的讲演题目是《两种自由概念》。这是我就任牛津大学教授讲席的致辞。它的要点是区分自由的两种观念,即消极与积极自由。关于消极自由,我指的是不存在阻碍人行动的障碍。除了由外部世界,或支配人类的生物的、生理的和心理的规律所产生的阻碍外,还存在着缺乏政治自由的阻碍——这是我的讲演的核心。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这些阻碍就是人为的,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消极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这种人为阻碍存在与否,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不被人为的制度、纪律或某些特定人类的活动所阻止,而自由地沿这条或那条道路前进的程度。
说消极自由仅仅意味着自由地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不够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可以简单地遵循古代斯多鳴派消灭欲望的方法,使自己从实现欲望的障碍中解放出来。但是这条路径,即逐渐消除会导致障碍产生的欲望,最后会导致人类逐渐失去其自然的、有活力的活动;换句话说,处于最完美的自由状态的人将是那些死者,因为在他们那里既不存在欲望也不存在障碍。但是我心目中的消极自由,指的仅仅是一个人能够顺着走的那些道路的条数,至于他走不走,那是另一回事。这是政治自由的两个基本含义的第一个。
有些人不赞同我的观点,坚持说自由必须是一种三重关系:我克服、清除或摆脱障碍仅仅是为了做某件事,即自由地做某个或某些既定的行动。但我不接受这种说法。当一个人身陷囹圄或被绑在树上时,他就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如此。这种状态中的人唯一寻求的,是打碎他的锁链,逃离监狱,他并不必然是为了实现某个特殊的行动。当然,在更大的意义上,自由意味着摆脱社会或其制度的统治,摆脱某种过分的道德或物质力量所施加的作用,或者摆脱任何关闭行动的可能性的东西——这些可能性本来是可以开放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免于……的自由”。
自由的另外一个核心含义是“做……的自由”。如果我的消极自由通过对“我被控制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得到限定,那么,自由的第二个含义,是通过对“谁控制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来限定的。既然我们说的是人为的障碍,那么我就可以问:“谁决定我的行为、生命?我是否能自由地依我选择的方式行事?或者,我是否处于别的控制力量的命令之下?我的行动是不是受父母、学监、牧师、警察的决定?我是不是处于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秩序、奴隶主、政府(君主制的、寡头制的和民主制的)的约束之下?我的行动的可能性也许受到限制,但是它们被如何限制?代表我的那些人是谁?他们可以使用的权力有多大?”
这就是我想要探讨的“自由”的两个核心含义。我认识到它们是不同的,是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的回答;它们虽然同源,但在我看来它们却并不冲突,也就是说对其中一种问题的回答并不必然决定对另一种问题的回答。
两种自由都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两者都必需受到限制,两种概念在人类历史上都可能被滥用。消极自由可能被解释成经济的自由放任,据此,矿场主以自由的名义被允许在矿井下摧毁儿童的生命,或者工厂主被允许去摧毁工厂中工人的健康与人格。但是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滥用,而不是这个概念对于人类的基本含义。同样,告诉一个穷人说虽然他支付不起,但他完全有自由在一家昂贵的饭店拥有一个房间,这么说无异于嘲弄。但是这种说法也是一种混淆。他的确有在那里租用一间房子的自由,但没有手段使用这种自由。而他之所以没有这种手段,可能是因为一种经济制度阻碍他获得比他现在更多的收入;但这是一种对赚钱的自由的剥夺,而不是对租用房间的自由的剥夺。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学究式的区分,但是对于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讨论却是非常关键的。
从历史上看,积极自由的观念甚至导致了更加可怕的滥用。谁对我的生命下命令?我。真的是我吗?无知、混乱、处处受无法控制的激情与的名义。这正是积极自由观念常常陷入的最大的滥用:不管专制来源于……领袖、国王、法西斯独裁者,还是来自极权式的教会或阶级或国家的主人,它都试图在人性中寻找被禁锢的“真实”自我,并“解放”它,以便这个自我能够达到那些发号施令者的水平。
这就回到了一种天真的观念: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我知道这个正确的答案而你不同意我,那是因为你无知;如果你知道真理,你必然会相信我所相信的;如果你想不服从我,只能说明你是错误的,因为那个真理并没有像显示给我那样显示给你。这种说法替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发指的压制与奴役形式辩护;而且这的确是积极自由观念的最危险、最凶残的含义,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世纪。
从那以后,两种自由观念及它们的被歪曲的形式,在西方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里,成为激烈的讨论与争论的中心,今天仍然如此。